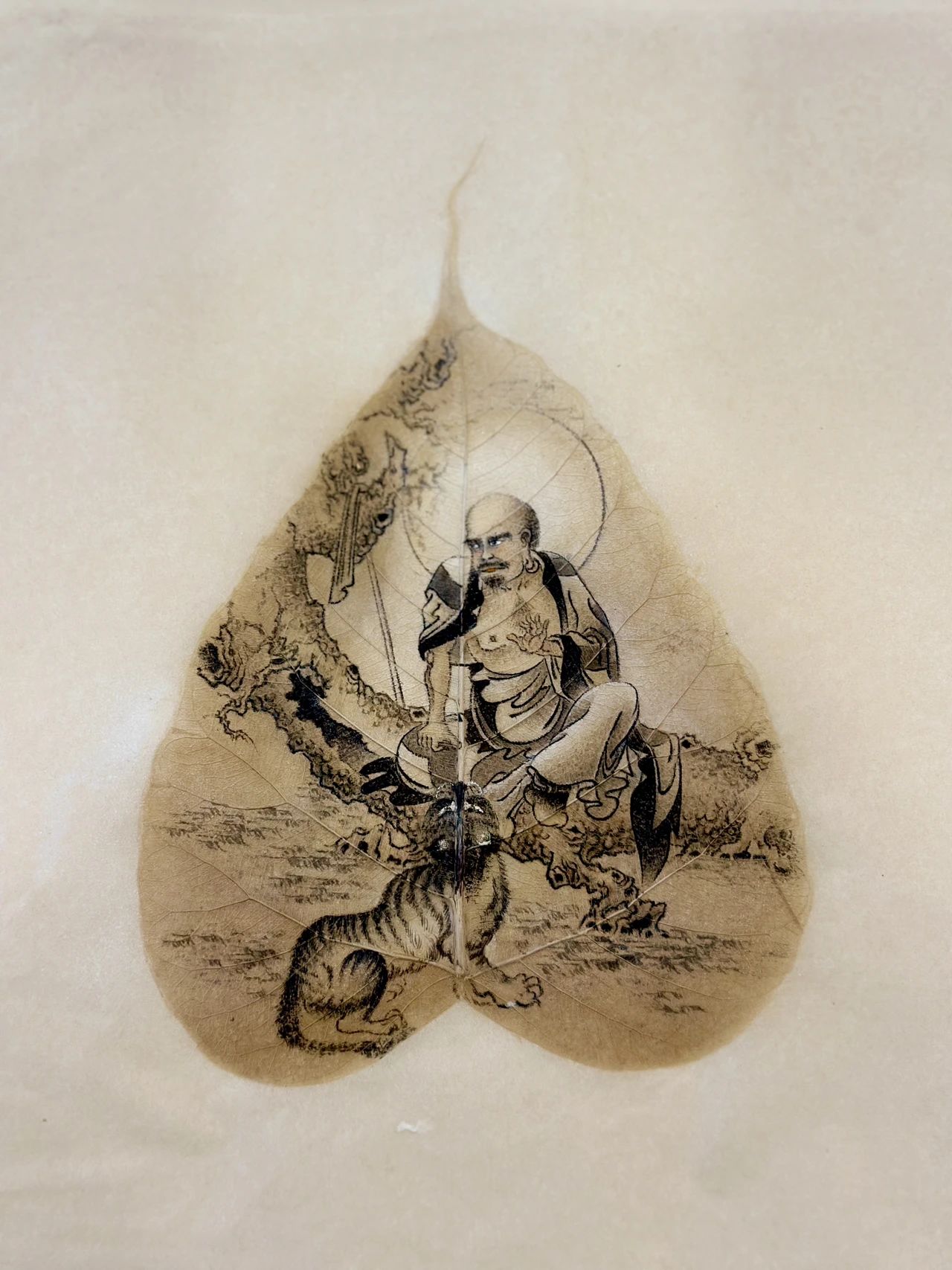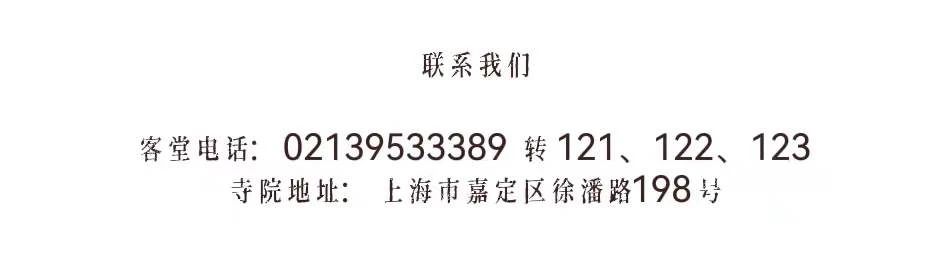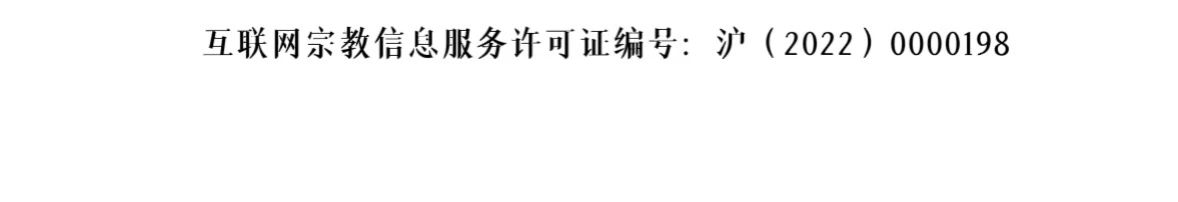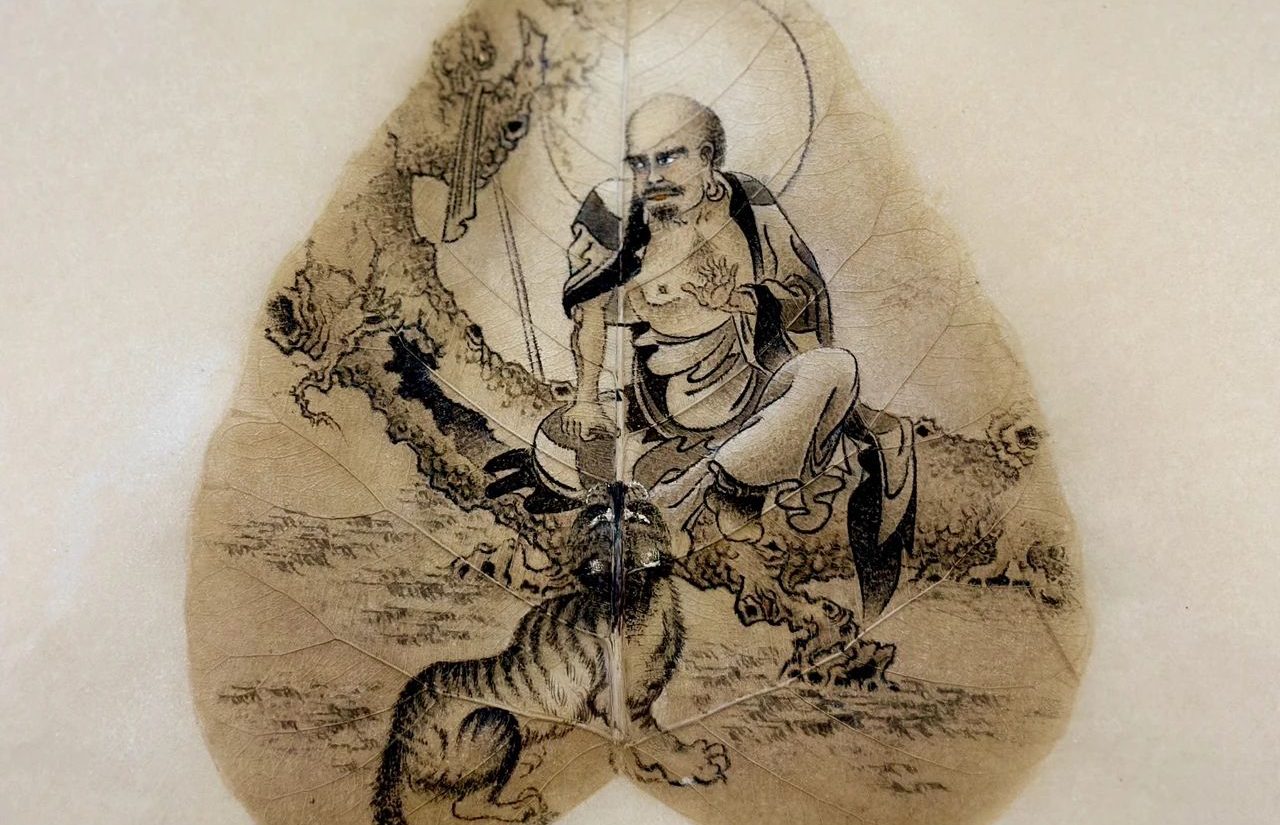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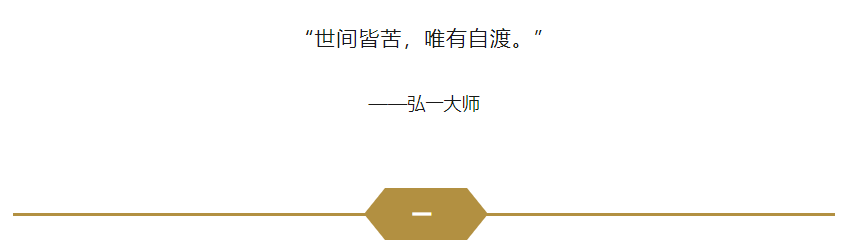
人类从死的刹那到生命创新那一关,恰同自初冬进入冬眠的虫,当他的假合之身变为白骨,他的生命已表现为另一种形式。生命是不死的,流转的,轮回的巨流。
现在,弘一大师开始钻入律藏的故纸里。他潜居玉泉,遍读“南山遗学”,并以《四分律》为中心,展开辐射式的演绎研究。
玉泉寺的长老印心、宝善,为这位艺术大师持“过午不食戒”,特地把午斋提到上午十一点来,以便使这位刚出家不足半年的比丘,维持他严净的戒行;同时,午斋之后,好使他小憩片刻,然后开始埋头苦修。
这些日子里,正是他舍俗后钻研佛乘、刻苦修道的巅峰,其态势是一日千里。
以大脑如李叔同这种多样天才,遁入空门,弄起佛学,僧林中任何角色,都只有呆望着那一条瘦长的身形,疾逝而去。那是所谓“望尘莫及”的!照佛家的轮回观说:只因夙慧深,善根厚,多生多世植慧植福,到今天,才有多方面的成就,这也不过是他多生来所储蓄的一顿丰美果实而已!
他日日如是,刻刻如是,除了早粥、午斋,全部时间支配在那间小佛堂里,他对佛学与学佛,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供献的!

佛堂的礼佛蒲团上,长跪一个僧人,上身笔直而瘦削,身披栗色袈裟,光顶芒鞋赤脚,正凝视堂上的佛像,低念某一种经文。
从背影看去,恰似多年前的李叔同。可是,这位和尚似乎未闻人声,袁希濂走进去,他依然长跪不起,口中低沉而清晰地随着手中小木鱼的笃笃声,一字一唱。袁希濂似乎为那种静境所折服,没有惊动他。
时间无休止地流走,袁希廉这时不由得怀疑起来。“这位和尚究竟是不是李叔同呢?” 他想问问,可是他不能那样放肆——在一座清静的寺院,扰乱了出家人的清修。
他向前走两步,站在和尚的右后方,只有几步,贪婪地扫视佛堂一周。
小佛堂,净洁无尘,二尺高的佛像、供桌、蒲团、青石铺的地面。
他等了快到一个钟点,和尚唱了一首偈子,起身了,向佛像顶礼三拜。之后熟练而无声息地卸下身上的袈裟,折成长方形,搭在左手臂上,便转过身,往袁希廉看看,淡淡地倾出一脸笑意。
“呀!叔同!”袁看出这位和尚正是当年的瘦桐——李叔同!
“希濂!”和尚说,“我们到里面小坐。”
说这话时,和尚便走到佛龛左侧,推开一扇小门,把访客引导入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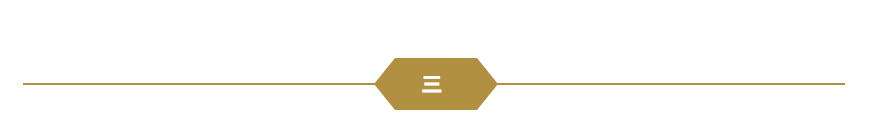
“真想不到,四年后的今天,你在这里落发遁入空门。”
“——这,倒是稀有的缘!”弘公终于道出了这句话,脸上顿时显得欢欣鼓舞。
“官场里的事,绊住了我。去年我便到杭州来了,一拖便是一年,可是,现在又要走了,现在,我特地来看看你的生活,同时告别。唉——人间离合悲欢,真像一场梦。”
袁希廉说到这里,师忽然抬起眼,向他睨视一刹。
“你前生也是个和尚!”
“我吗?”袁乍听这句话,心头一怔,瞬息若有所悟地说,“我做过和尚?”
“请珍重!忙里偷闲,晨昏念佛,自有归处。”
“噢,不错,不错!”袁连声诺诺。
“在佛书里,有一种《安士全书》,不可不读,那是一部为居士们开辟思想栈道的名作。”
《安士全书》,《安士全书》!”袁一再地默记。
“你点破了我的黑灯笼!”袁希廉感激地站起身,“我未能脱俗呀,老朋友!我这样叫你可以吗?”
弘公放下袁的一席话,庄严地从书架上层,取下袈裟,“我的下一课时间到了——人身难得,是万古一瞬的因缘;佛法难闻,是历劫不遇的际会。错过了,没有人能承担这份过失,阿弥陀佛,珍重!”
袁手足无措地退出佛堂,“叔同,后会有期了。你的照应,使我永志不忘。”他们在暮色苍茫中告别。
师送袁出门,站在石阶上,待袁希濂走出他的视野,不禁叹息一声。
“菩萨也有隔阴之迷,何况一个根基未深的凡夫?”他这悚然一念,通过脑中;然后,便匆匆走下石阶,向大殿走去。
——节选自《弘一大师传》,陈慧剑著